

十七年
十七年
第一部:求助的父母和奇怪的少女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一连收到了好几封来信,内容相同。
由于我生活的接触面极度,所以收到的信件也极多,送信的邮差,每天都是用细绳把我
的信扎成一扎。
除非是我特别在期待着的信,或是一看信封,就知道是熟朋友寄来的,不然,我都不
拆,因为实在没有那么多闲时间。
大多数的情形下,白素每天都会抽出一定的时间拆看这些信件。她说:“人家写信给
你,总有一定的目的,何必令人失望?就算不回信,也该看看人家说些甚么。”
我自然不会反对她这样做。
那一批同样内容的信的第一封,就是她给我看的。
当时她道:“这封信很有意思。”
我接过信,先看署名:一个不知如何才好的妈妈。这是一个相当吸引人的署名,表示了
这个作为妈妈的人,内心一定焦急之极。
当时我道:“这封信,是不是应该转到甚么青年问题中心去?”
白素瞪了我一眼:“你看完了信再发表意见!”
我高举手,作投降的手势,信的内文如下:
“卫斯理先生:
我知道你不会轻易帮一个陌生人,除非这个陌生人来自外星。你真是不公平,地球上有
那么多你的同类需要帮助,你置之不理,老是去帮助不知来自何处的外星人,难怪有人怀疑
你根本也是外星人。”
我看到这里,咕哝了一句:“岂有此理!”
白素微笑了一下,像是早已料定了我会有这样的反应一样。我再看下去:
“看了你记述的《洞天》,我对李一心的父亲李天范先生,寄以无限的同情,一个家庭
之中,有一个异乎寻常的孩子,十分痛苦:作为父母,完全无法知道自己的孩子在想些甚
么,做些甚么,为甚么而来,何时会突然失去他。”
我摇了摇头,向白素望了一眼:“全世界的父母,似乎都有同样的麻烦。”
白素向我作了一个手势,示意我看下去。
“我有一个女儿,异乎寻常,这孩子,自小就怪极了,比你在《洞天》中记述的李一心
还要怪,李一心只不过对佛庙的图片有兴趣,而我的女儿,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特异,她在
周岁的时候,就会时时支颐沉思,可是却又从来不肯对我们说她在想甚么。
“有时我偷偷留意她,看到她在沉思中,表情十分丰富,有时现出甜蜜的笑容,有时却
又愁容满面,有时也会暗暗垂泪,从小到大,一直是这样,令得我们不知如何才好,而近一
年来,她的行动更是怪异——她再有一个月,就满十七岁,一切都正常,没有人不说她美丽
出众,可就是怪行为越来越甚,甚至令我们感到害怕。
“卫先生,看了很多你记述的故事,我和外子商量过,他是一个电机工程师,已快届退
休年龄了,本来一直是你笔下的那种科学家——只相信现代人类科学已经证明了的事,但是
我们的女儿实在太怪,所以他也不得不承认,我们的女儿,可能有着类似前生的记忆,这种
记忆,是她自己的秘密,而我们全然无从得知。
“卫先生,不怕对你说,我们曾经失去过一个女儿,那是多年前极惨痛的经历,实在不
能再承受一次类似的打击。所以,冒昧写信给你,希望藉你的智慧,和锲而不舍追求事实真
相的精神,帮助我们,如果能得到你的帮助,感激莫名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一个不知怎样才好的妈妈敬上。”
看完了信之后,我道:“嗯,对我的恭维,恰到好处。”
白素摇了摇头,作出“不忍卒听”的样子。我道:“这个少女,如果真的有前生的记
亿,有几个朋友对这方面有极浓的兴趣,可以介绍这位妈妈去见他们中的任何一个。“
白素倒同意了我的说法:“是,很多人都可以帮她忙,陈长青怎么样?他研究那些石
头,不会有甚么结果,也可以告一段落了?”
我摇了摇头:“不,不如介绍给甘敏斯,那个灵媒。或者,普索利爵士?这都是曾和我
们一起探索、并且肯定了灵魂存在的人。”
白素望了我一眼:“你自己完全没有兴趣?”
我耸了耸肩:“可能只是做母亲的人神经过敏,我不想浪费时间。”
白素道:“好,那就回信给她,请她随便去找一个人求助好了,反正有回邮信封在。”
事情就这样决定了。
三天之后,收到了第二封信。
“卫先生,很感激你的来信,我们的困难,相信除了你之外,无人可以解决,我们不会
去找那几位先生,只在等你的援手……”
信中还说了一大串他们如何焦急,如何彷徨,词意恳切动人,最后的署名变成了”不知
如何才好的父母同上”。
我看了之后,相当不快:“这算甚么?求人帮助,还要点名!我介绍给他们的那几个,
他们以为全是普通人?哼,没有我的介绍,那几个人根本不会睬他们。”
白素不置可否:“或许那女孩只是精神上有点不正常?有前生记忆的人,毕竟不是很
多,可以请他们去看看梁若水医生。”
我闷哼了一声,说道:“随便他们吧。”
白素自然又回了一封信,可是那一双“不知如何才好的父母”,却真的固执得很,一直
在写信给我,一天一封,每封信都提出了同样的要求。大抵自第五六封信开始,连白素也没
有再回信了。
这件事,我没有怎么放在心上,因为来信提出各种各样要求的人很多,那一双父母虽然
说他们的女儿“怪异”,一个人自孩提时代起,就喜欢沉思,至多只能说她早熟,很难归入
怪异一类。
然后,就是陈长青来访,他胁下挟了一只文件夹子,我一看到他就问:“那些石头的相
片,你弄了多少幅了?”
陈长青摇头叹息:“超过一万幅了,真是闷得可以,每天做同样的事,一点变化也没
有,这样下去,人会变成疯子。”
我笑道:“或许你那一万幅照片,幅幅都是伟大的预言。”
陈长青一瞪眼:“甚么或许,根本就是,只不过全然无法知道它们的内容,就像手上有
一本天书,可是看不懂,就等于没有。”
我拍着他的肩,安慰着他:“暂时停一下手吧,你和温宝裕这小鬼头在一起,还怕没有
新鲜的花样玩出来么?”
陈长青笑了起来,拍了拍文件夹:“你还记不记得,由于报纸上的一段怪广告,出售木
炭的,结果引出了多大的故事来?”
我自然记得,那是《木炭》的故事,我道:“怎么样,又在广告上有了新发现?”
陈长青连连点头,放下了那文件夹,打开,我看到其中是剪报,整齐地贴在纸上,一共
有十几张纸,每张纸上,都贴着十公分见方的剪报十余张不等,一共至少有两三百份,看了
一眼,所有广告的内容全一样:
“家建,你一直没有回家,我们之间的约会,你难道忘记了?还是你迷失了?我相信我
们之间的誓约,我们两人都一定会遵守,我不信你会负约,见报立时联络,我已回家了。我
实在已等得太久了。知名。”陈长青在我看的时候,翻动了一下报纸,所有纸上贴的,全是
同样的广告。
我不禁“哈哈”大笑了起来:“陈长青,你越来越有出息了,这种广告,报纸上哪天没
有?嗯,家健是一个男孩子名字,一定是一个女孩子登的广告,在找那个负了约的男朋
友。”
陈长青道:“我有说不是吗?”
看到他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,我倒也不能说甚么,用询问的目光看着他:“有甚么特别
呢?”
陈长青指着广告,用手指在广告上弹着,发出“拍拍”的声响来:“这一个叫家健的男
孩子的父母,我认识,一个……远房的亲戚。”
我翻着眼,因为这仍然没有甚么特异之处。
陈长青“哼”地一声:“说出来,吓你一跳,这个叫家健的男孩子,十七年之前就已经
死了,一个人死了十七年,还有人登报纸来找他,你说,这件事,还不算奇特?”
我听了之后,不禁呆了一呆,真的,可说是十分奇特,我道:“嗯,有点意思。”
陈长青得意起来:“本来嘛,这个广告,在本地大小报章士都有刊登,我自然不会注
意,家健的父母看到了,开始留意,留意了将近一个月,知道我对于各种疑难怪事,素有研
究,所以才来请教我,我一听这件事大可研究,所以来找你——“
陈长青口沫横飞地说,我作了好几次手势,令他住口,他都不听,我只好大喝一声:
“闭嘴!”
陈长青总算住了口,眨着眼,神情恼怒。
我也感到相当程度恼怒:“那个叫家健的男孩子的父母,看到了这个广告,就认为登广
告的人,是在找他们十七年前死了的儿子?”
陈长青道:“是。”
我又发出了一声大喝:“他们混账,你也跟着混账,你可知道,中国男性之中,用『家
健』这两个字做名字的人有多少?怎见得这个家健,就是他死去的儿子?”
我的驳斥,再合情合理也没有。别说只有家健这样的一个名字,就算连着姓,只要姓不
是太僻,也就有不知多少王家健陈家健李家健张家健!陈长青一声不响,听我说着,这次他
脾气倒出奇的好,等我讲完,他才道:“你以为我没有用同样的问题问过他们?”
我笑了起来:“好,他们用甚么样的回答,使你相信了这个家健,就是他们死了十七年
的儿子?”
陈长青眨着眼:“这就是我来见你的目的,听他们亲口向你解释,总比由我转述好得
多。”
我摇着头,表示没有兴趣,陈长青道:“看起来,他们的说法一点理由也没有,你能想
像得出他们如何会肯定了这个被寻找的家健,就是他们儿子的理由?”
我笑道:“一猜就猜中,他们一定是想儿子想疯了,所以才会有这种想法。”
陈长青道:“是,他们的确为了他们孩子的死,极其伤心,伤心的程度,历十七年如一
日,但是那绝不是他们凭空的想像。你现在在忙甚么?跟我去走一次,花不了你多少时
间。”
我仍然摇着头。陈长青这时,有点光火了,涨红了脸,飞快地眨着眼:“卫斯理,想想
你自己,不论有甚么事要我做,半夜三更打个电话来,我可曾有一次在牙缝里迸出半个
『不』字来?虽然不曾两胁插刀,赴汤蹈火,但可以做的一定去做,难得我有点事请你帮个
小忙,你就推三搪四,摆他妈的臭架子!”
他语发如联珠,虽然说的话相当难听,最后连骂人话都出来了,但是想起他多次热心办
事的情景,我倒也真的不好意思,忙道:“是,是,是,陈先生请暂息雷霆之怒,小可这就
跟你去走一遭。”
陈长青一听我答应了,立时反嗔为喜,向我抱拳为礼,立逼着我走。我们才来到门口,
白素恰好开门进来,我道:“陈长青找我有事情。”
白素“嗯”地一声,反手向门口指了一下:“那个小姑娘,已经一连三天,在我们门口
徘徊不去,看来满腹心事。”
那时,我们都在屋内,但由于白素才开门进来,所以门开着,看出去,可以看到一个穿
着浅蓝色校服的少女,大约十六七岁,眉清目秀,有着一股异样的秀气,正在对街,用十分
缓慢的步伐,来回走着,不时的向我的住所,望上一眼。
我皱了皱眉,陈长青忙紧张兮兮地道:“人不可貌相,记得那个瘦瘪老太婆,竟然是很
有地位的特务,莫不是有些特务组织,还不肯放过你?”
我“呸”地一声:“哪有那么多特务机构,那座石头山被他们搬了一半去,还有甚么好
来找我的?”
我一面说,一面还在打量着那少女,这样年龄的少女,总是活泼而充满了青春气息的,
可是这个少女,可能由于她比较瘦削,而且又有十分清秀的脸容,看起来,像是整个人都充
满了愁思。
我对白素笑了一下:“少女情怀总是诗,她如果有甚么为难的事,我看我和陈长青,都
无能为力,还是你去暂充一下社会工作人员吧。”
白素笑了起来:“我正有这个意思,但是还要再观察一下。”
我和陈长青走了出去,看到对街那小姑娘,立即向我们望了过来,可是望了一下,非但
没有向前是来,反倒后退了两步。
陈长青低声道:“卫斯理,这少女真是有事来找你,可是却又不敢。”
陈长青的观察力相当细致,我也同意他的分析:“白素会处理的。”
陈长青叹了一声:“年纪那么轻,会有甚么心事。”
我们一起上了陈长青的车,由他驾驶,在路上,他只告诉了我一句话:“我们要去见的
那对夫妻,姓得相当怪,姓敌,敌人的敌,你听说过有这个姓没有?”
我摇了摇头:“多半不是汉人,才有这样的怪姓,我知道有一位工艺非常出众的玉雕
家,姓敌,叫敌文同。”
陈长青陡然用十分怪异的眼光望着我,我忙道:“难道就是他?”
陈长青一扬手:“不是也是谁?姓敌的人,全世界加起来,不会超过三个。”
我笑了一下,敌文同是相当出色的玉雕家,曾经用一块上佳的翠玉,雕成了一只蚱蜢,
蚱蜢作振翅的动作,翼薄得透明,连精细的纹理都清晰可见,拿出来展览时,见者无不钦
佩。当然,他并不是甚么大人物,也不会有很多人知道他的名字。
我问:“这位敌先生,是你的亲戚?”
陈长青笑着:“敌先生娶的妻子,是我姑丈那里的一个甚么表亲,这种亲戚关系,真要
是扯开去,所有中国人全是亲戚,不过我和他经常有来往,我极欣赏他的玉雕艺术,等一
会,你就可以看到一件极伟大的玉雕品,他花了十七年时间,还未曾全部完成。“
我不经意地问:“十七年,怎么老是十七年?”
陈长青叹了一声:“十七年前,敌家健意外丧生,敌文同哀痛欲绝,就开始了这件伟大
的玉雕工作,他把他全部的财产,去换了一块将近一吨重的白玉,白玉的质地十分好,他就
开始——“
我已经料到了:“开始雕他儿子的像?”
陈长青点了点头:“一座全身像,和真人一样大小,据他说,所有的一切,完全和十七
年前的敌家健一样。”
我叹了一声:“作为思念早逝儿子的父亲,这位敌先生的作为,真是罕见。”
陈长青道:“是啊,所以我也很受感动,一直在津贴他的生活,使他在生活方面,尽量
舒服,好使这个空前伟大的玉雕,得到完成,你看到了那玉雕像,就会知道那值得,在这个
雕像之中,充满了上一代对下一代的爱。”
我笑了起来:“你快可以改行做诗人了。”
陈长青有点忸怩:“是真的。”
说话之间,车子已经驶离下市区,我知道陈长青有的是钱,他既然说维持敌文同的生
活,那么敌文同生活一定不会坏,可是我也没有想到,好到这种程度。
当车子在一幢看来相当古老,但是极有气派的大屋子的花园门口停下来之际,陈长青也
留意到了我惊讶的神情,他解释道:“屋子本来是敌文同的,他押给了银行,我替他赎了回
来。”
车子停下,我们下了车,四周围的环境,极其清幽,那花园也相当大,有许多比两层屋
子还高的大树,其中几株石栗树,正开满了一树艳黄色的花朵,映着阳光,看来十分灿烂。
那时,正是初夏时分,花圃上,开着各种各样的花,把古老的屋子点缀得生气勃勃。
我一面跟着陈长青向前走去,一面道:“环境真不错,生活在这样环境中的人,不应该
是一双哀伤的老年夫妇。”
我的话才说完,在一丛灌木之后,就传来了一个妇人的声音:“我们是为家健而活着,
家健生前,不喜欢的事,我们不做,他喜欢的一切,我们照做,就像是他随时会回来一
样。”
声音听来十分平静,但是在平静之中,却又有看一股极度的哀思,只有把哀愁当成了习
惯的人,才会有这样的语调。而哀伤已成了生活中的主要部分,哀伤的深刻,也可想而知。
我循声看去,说话的女人,甚至没有直起身子来,仍然弯着腰,在修剪一簇康乃馨花,
她满头白发,陈长青立时叫了她一声,她直起身子来。大约不到六十岁,样子和衣着都很普
通,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的眼神,充满了迷茫和无依,但是却又像在期待着甚么。
陈长青指着我:“敌太太,这位卫斯理先生,是我要好的朋友。”
敌太太礼貌地向我点着头,抬眼看,放下了手中的花剪:“请进去坐,长青老说起
你。”
我也客套了几句,和他们一起进了屋子。一进屋子,就是一个相当大的厅堂,可是那么
大的一个厅堂之中,完全没有家俱陈设,只有在正中,有一张桌子,桌子上放着许多工具,
看来是雕琢之用。
在桌子旁边,站着两个人,一个六十出头,身形相当高大,一头白发的老人,和一个身
形和他相仿的年轻人——别笑我,我一眼看去,真以为是两个人面对面地站着,而老者还流
露出一片慈爱的神色,正在年轻人的脸颊上,轻轻抚摸。
但是,我再看多一眼,我不禁发出了“啊”地一声,知道站在那里的,只是那个老者,
那“年轻人”,只是一座和真人一样的玉雕像,但是在雕像上,却又穿着真的衣服,所以才
会在最初的一眼,给我这样的错觉。
那玉雕像生动之极,神态活现,充满了生气,我从来也未曾在一座雕像之中,看到过这
样的生态,即使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艺术大师的作品,也不会给人以如此生动之感。
或许,由于雕像是白玉雏成的,所以流动着一种自然而晶莹的光采,这种光采,就给人
以活生生的感觉。
我不由自主赞叹了起来:“真伟大。”
那位老先生,自然就是敌文同,他转过脸来,茫然的神情,和略带润湿的双眼,眼中布
满了红丝,更显出他精神的忧郁,他现出了一个十分苦涩的笑容。陈长青忙替我们介绍,我
在寒暄了几句之后,指着那雕像,由衷地说:“真是不虚此行,这雕像太不平凡了。”
敌文同叹了一声:“一万座不平凡的雕像,也及不上一个平凡的活生生的人。家健要是
还在世的话,今年是三十九岁了。再过一个月,就是他的生日——“
他在这样说的时候,向他的妻子看去,她立时道:“还有二十七日。”
敌文同又道:“三十九岁的人,当然早就成家立室,只怕——“
他的妻子立时接了上去:“孩子也有好几个了,大屋子里有孩子,多热闹,家健小时
侯,屋子里——“
他们两夫妻自顾自地说着,我和陈长青互望了一眼,陈长青可能习惯了这种情景,但是
我却无法掩饰我心头的骇然。
同样的对话,在他们之间,一定重复过不知多少次了~
看起来,还会不断重复下去,这两个人,完全生活在梦幻中,生活在充满哀痛的梦幻
中,一切只为思念他们逝去了的儿子而活着,这实在是相当骇人的一种不正常,可是却又实
在不能指责他们甚么。
我见过不少失去孩子的家庭,可是像这样的情形,我却还是第一次经历。
他们两人不断地在讲着,讲来讲去,几乎每一句话中,都提及“家健”这个名字,我和
陈长青在旁,不知如何插口,只好眼睁睁地望着他们,听他们讲他们的孩子,十七年前已经
去世了的孩子。
足足过了十分钟之久,陈长青才忍不住咳嗽了几声,大声道:“敌先生,卫先生不相信
那广告,是有人为敌家健刊登的。”
敌文同夫妇,像是如梦初醒一样,停止了谈话,向我们望来,敌太太甚至抱歉地笑了
笑:“真是,一谈起我们的孩子来就没有完,连贵客都忘了招呼,真不好意思,卫先生莫见
笑。”我怎会“见笑”?我骇然还来不及,眼前的一切,虽然没有甚么恐怖诡异的成分,可
是给人心头的震撼,却无与伦比。
敌文同道:“来,来,请到我的书房来,我有事要请教卫先生。”我们一起离开了大
厅,进入了一间书房之中,出乎意料之外,书房中的书籍极多,古色古香,一点也不像是一
个雕刻家的书房。
陈长青道:“敌先生是古玉专家,对各种各样的玉器,有着极丰富的知识,世界上好几
个大博物馆,都聘请他当顾问。”
我看到在书桌上,有不少古玉件放着,还有不少有关玉器的书籍,我道:“古玉鉴定是
一门极深的学问,敌先生一生与玉为伍,真不简单。”
敌文同客气了几句:“玉的学问真是大,人类,尤其是中国人,早就和玉建有十分奇怪
的感情,我坚持用玉来雕刻家健的像,就是想把自己对家健的感情,和人对玉的感情结合起
来。”
我没有敢搭口,因为不论甚么话题,他都可以带出家健的名字来,若是再一搭腔,只怕
他滔滔不绝起来,不知如何收科。
敌文同请我们坐下,敌太太端着茶和点心,带着抱歉的笑容:“没有甚么好东西招待卫
先生,只有家健喜欢吃的一些点心。”
我有点坐立不安,已经死了十七年的敌家健,看来还真像是生活在这屋子中。
敌文同叹了一声,总算话题转到了正题上,可是一样,还是离不了家健,他道:”卫先
生,相信你已经知道,我们在甚么样情形之下生活。”
我苦笑了一下,心想劝他几句,但是却又实在不知道如何说才好,敌文同和他的妻子,
长时期以来,在痛苦哀伤之中生活,又岂是我三言两语,能把他们的痛苦减轻的?如果我安
慰他“人死不能复生,不要太伤心了。”他一定会反问:为甚么要死,为甚么那么多人活
着,偏偏家健死了,他死得那么年轻,为甚么……
所以我根本不说甚么,只等他说下去。敌文同缓缓地道:“家健虽然离开我们已经有十
七年,可是我们每一分、每一秒都在想念他,这种情形之下,我们忽然看到报上出现了一个
广告,有人在找家健,加以注意,那是自然而然的事。”
我点了点头,表示同意,可是我同时,也小心翼翼地提醒他:“敌先生,家健是一个极
普通的男孩子名字。”
敌文同倒不反对我的说法:“是,家健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,但既然和我们的孩子同
名,我们也就注意,开始时,我和妻子只不过说:啊,这个人和我们的孩子同名,他不知道
到甚么地方去了,累得一个女孩子要登报找他。我们的家健如果在,一定不会辜负女孩子的
情意……诸如此类的话。”
我用心听着,在他们两人之间,看了这样的广告,有那样的对白,是自然而然的事。
敌文同继续道:“可是,广告一天又一天登着,而且,我们留意到了大小报章上都有,
这就引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。”
我仍然没有表示甚么意见,只是心中在想:敌文同的反应,自然还是基于他对儿子的怀
念,要不然,寻常人看了这样的广告,不见得会有甚么好奇心。
敌文同道:“每天,我和妻子都要说上好几遍:啊,还没有找到家健,可惜我不知道如
何和登广告的人联络,有一次我说,和那女孩子联络一下。我妻子说:可以到报馆去问一
问,或许登广告的人,会在报馆留下姓名地址,我一想很有道理,反正每家报纸都有这样的
广告的,于是就去查问。”
我“嗯”地一声:“一般来说,报社是不会答覆这样的询问的。”
敌文同道:“是啊,我连走了四间报社,都遭到了礼貌的拒绝,我已经不想再进行了,
在归途中,又经过了一家报馆,姑且再进去问问,一进去,就遇上了熟人,是我的一个世
侄,现任该报的副总编辑,朝中有人好办事,他一听我的来意,就带我到广告部,广告部的
职员说:来登广告的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学生,样子很清秀,可是却没有留下姓名地址,广
告费是先付了的。”
我一直在耐心听着,虽然他说到现在,仍然未曾说到何以他肯定那个家健,就是他的儿
子。非但未曾提出强而有力的证据,而且越来越不对头了。
我道:“如果登广告的是一位少女,那么,这个家健,更不可能是令郎。”
敌文同叹了一声:“卫先生,当时,我并未想到这个家健,就是我的家健,所以是谁去
登广告,对我来说全一样。”
他这样说,自然是表示事情在后来,又有变化,我自然只好耐着性子听下去。敌文同
道:“那职员一面说,一面翻查着资料,说:广告的原稿还在,请看。他把一张普通的信纸
递了给我,我一看之下,整个人都呆住了。”
敌文同讲到这里,现出了十分激动的神情,他的妻子忙过去握住了他的手。
我也不由自主,坐直了身子。
敌文同深深吸了一口气:“那张信纸上写的就是那段广告,字迹很娟秀,出自少女之
手,殆无疑问,令我震动的是,在原稿上,家健这个名字上,有一个字被划掉了,可是还可
以看得出来,那是一个『敌』字,也就是说,那个家健姓敌,卫先生,敌是一个僻之又僻的
怪姓,敌家健,就不可能是别人,一定就是我的儿子,我把广告的原稿,影印了一份,你请
看。”
他双手在不由自主发着抖,取了一张影印的纸张,放在我的面前。
不错,那就是那份广告的原稿,有不止一个字被改动过,都用同样的方式划去,包括那
个“敌”字在内。这个“敌”宇,加在“家健”两字之上,自然本来是连名带姓的“敌家
健”,被划去了之后,才变成了报上刊出来的那样,只有“家健”两个字。
我呆了半晌,陈长青在一旁道:“自然,也不排除同名同姓的可能性。”
敌文同夫妇异口同声道:“不会,不会。”
陈长青道:“也不会有人和你们在开玩笑,要是开玩笑的话,就不必把敌字划掉了。”
我伸了伸身子:“敌先生,你真肯定没有别人姓敌的?”
敌文同道:“可以肯定,这个姓,是我祖父自己改的,他不知在甚么事上受了刺激,就
改了这个姓,而我们家一直是一脉单传,如今……我过世之后,世界上就再也不会有姓敌的
人,要是家健在,可能开枝散叶的话,姓敌的人,还可能多几个。”
这事情,真有点怪,我略想了一想:“其实,要和那个登广告的少女联络,也十分容
易,就在他的广告旁边,登一段广告好了。”
陈长青听得我那样说,顺手把一份报纸,移到了我的面前,原来他们已经这样做了,在
寻找家健的广告之旁,有着另一段广告:“小姐,我们是家健的父母,请和我们联络。”下
面是地址和电话。
敌文同摇头:“真奇怪,照说,如果她急于找家健,一见了这段广告,就该立即和我们
联络才是,可是已经一个星期了,别说不见人,连电话也没有一个。”
陈长青瞪着我:“你有甚么解释?”
这件事要一下子作出确切的解释,不是容易的事,我心中仍在想,那个“敌”字,可能
不是表示姓氏,那少女要找的家健,根本不是敌家健,一个少女怎么可能要登报找一个死去
了十七年的人?所以,当她看到了敌文同的广告之后,自然觉得那是胡闹,不会来联络。
我本来想把我想到的,直接讲出来的。可是我考虑到,敌文同夫妇,在丧子之后,一直
在极度痛苦中生活,有人找他们死去了的儿子,这件事虽然不能使他们的生活有任何改变,
但是至少,是在一潭死水之中,掷下了一块石子,多少能引起一点水波,对他们目前这样的
生活来说,未始不是好事,又何必去令他们失望?
所以,我迟疑着未曾说甚么,敌太太在这时候道:“文同,要不要把那个小姑娘……那
个奇怪的姑娘来找家健的事,对卫先生说一说?”
我怔了一怔:“甚么奇怪的小姑娘?”
敌文同皱着眉:“这件事,也真怪,记得那是家健死后的十周年忌辰,为了怀念家健,
每年忌辰,我们两夫妇,都……都……”
他讲到这里,喉头梗塞,说不下去,敌太太也开始拭泪。这种场面,自然令人感到黯
然。我忙道:“我知道,天下父母心……还是说说那个奇怪的小姑娘吧。”
敌文同“嗯”了一声:“那时侯,我玉雕还未完成,客厅还有着家俱陈设,祭奠的仪式
也在那里举行,我们没有甚么亲友,只有我们两人,对着家健的遗像和遗物,默默垂泪,忽
然,我们听到了除了我们的辍泣声外,还有一个人在哭,我们回头看去,看到一个十岁左右
的小姑娘,瘦伶伶的,也不知道她是怎么进来的,也望着家健的遗像在哭着……”
------------------
第二部:相约来生爱意感人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敌文同夫妇,一看到忽然多了这样的一个小姑娘,心中真是讶异莫名,一时之间,也忘
了悲痛,敌太太首先问:“小妹妹,你是甚么人?”
那小姑娘并不回答,只是怔怔地望着敌家健的遗像,流着泪。
这种情景,十分诡异,敌文同夫妇连连发问,可是那小姑娘只是一声不出,反倒未得敌
文同夫妇的准许,过去抚弄敌家健的遗物,一面抚弄着,一面泪水流得更急。
敌文同夫妇给那小姑娘的行动,弄得骇异莫名,敌文同忍不住又问:“小姑娘,你认识
家健?”
他这句话一问出口,就知道不是很对头,因为那小姑娘看来,无论如何不会超过十岁,
而敌家健死了也有十年,怎么会认识?
所以,他立时又改口问道:“小妹妹,你今年多少岁了?”
那小姑娘仍然一声不出,敌文同夫妇不知如何才好,只好由得那小姑娘去,大约过了半
个多小时,小姑娘才忽然向他们问了一句话。
那小姑娘出现之后,一直未曾开过口,两夫妇几乎怀疑她是哑子了,但这时一开口,却
是声音清楚玲珑,十分动听。
她问的那个问题,也令得敌文同夫妇,震呆了好一阵子,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。
那小姑娘指着遗像问:“他一直没有回来过?”
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,但实在没有法子回答,两人震呆了一阵,敌文同悲哀地道:“小
妹妹,这是我们的儿子,他死了,今天是他去世十年的忌辰。”
小姑娘对敌文同的话,没有甚么特别的反应。敌太太对小姑娘的话,却又有不同的理
解。
本来,对一个只有十岁左右的小女孩,不应该说甚么,但是敌太太感到,这小姑娘对自
己的儿子的死,好像也感到十分悲悼。
敌老太太叹了一声:“小妹妹,你说他有没有回魂、托梦甚么的?唉,没有,我们无时
无刻不在思念他,但是……他真忍心……不曾回来过。”
小姑娘听到了这样的回答,大眼睛忽闪忽闪,泪珠涌了出来。
在敌文同夫妇还想再问甚么时,她突然转过身,向外疾奔了出去。
由于这小姑娘的言行,处处透着怪异,敌文同夫妇,自然立即追了出去,可是他们毕竟
上了年纪,奔跑之间,哪有小孩子来得快捷?等到他们追到了门口,那小姑娘早已爬过了铁
门,奔到了路上。
他们两人大声叫着,要那小姑娘回来,可是小姑娘连头都不回,一下子就奔得看不见
了。
事后,敌文同夫妇在附近找着,又捱门涯户,去拜访附近的人家,他们以为,那小姑娘
一定住在附近,在他们的屋子附近,有几条乡村,虽然那小姑娘看起来,不像是乡下人家的
孩子,可是他们连那几条乡村都没有放过。
而且,他们还渐渐扩大寻找的范围,足足找了一年,一点结果也没有,显然那小姑娘并
不从附近来,他们找寻的范围,已经远及十公里之外了。
一年之后,又是敌家健的忌辰了,敌文同夫妇都怀着希望,希望那小姑娘会再出现,可
是他们失望了,那小女孩没有再出现。
而且,以后,一直也未曾再出现过。
敌文同讲完了那“奇怪的小姑娘”的事,陈长青一面眨着眼,一面望着我:“我第一次
听到这个小姑娘的事,就认为那小姑娘,一定和家健认识。”
陈长青明知那小女孩的年龄,不可能认得敌家健,他还要坚持如此说,那么他的用意,
其实也很明显。他的意思是,那小姑娘在一种特殊的情形下,认识敌家健。
陈长青接着又道:“有两种可能,一是家健死了之后,曾和这小姑娘有着某种方式的接
触。其二,是这小女孩的前生——“
他讲到这里,向敌文同夫妇望了一眼。陈长青神态已经够怪,可是敌文同夫妇的反应更
怪,他们两人,不约而同,现出了极其愤怒的神情。
我不知道陈长青的话有甚么得罪他们,而且陈长青的话只说了一半,并没有讲完。陈长
青一看到敌又同夫妇面如玄坛,一副怒容,就不想再说下去。我忙道:“前生怎么样?”
陈长青吞了一口口水,才道:“有可能前生认识家健。”
敌太太这时,陡然叫了起来:“不会,你别再在我面前说那小女孩的前生是王玉芬。”
敌文同也立时瞪大了眼,充满敌意,彷佛陈长青如果再多一句口,他就要跳起来,饱以
老拳。
这更使我感到讶异,陈长青对敌文同十分好,连他们住的房子,都是陈长青出钱赎回来
的,而这时,他们对陈长青的态度,可以说坏到极点,而这一切,自然由于那个叫王玉芬的
女孩子所引起,这个王玉芬又是甚么人?为甚么敌文同夫妇不准陈长青提起她?
陈长青这个人,就是有这个好处,人家对他的态度如此之坏,但是他还是像受了冤屈的
小孩子:“我又没有说她是王玉芬,我只不过说,她前生,可能认识家健。”
敌文同甚至额上绽起了青筋,哑着声喝道:“别再在我面前,提起这个名字。”
陈长青飞快地眨着眼,不再说甚么,我向他望去,他也向我望来,同时,向我作了一个
手势,暗示我先别问,等会他会解释。
我也只好暂存心中的纳闷,一时之间,因为敌文同夫妇的态度异常,书房中陡然静下
来。过了好一会,两夫妇才又异口同声,向陈长青道歉,陈长青叹了一声:“算了,你们的
心情我明白,这……不必去说它了,总之,这个小姑娘有点古怪!”
敌文同夫妇又转而向我道歉,我讽刺了他们一句:“你们又没有得罪我,连陈先生都那
么大量,我有甚么关系?”
一句话,说得他们两人,满脸通红,唉声叹气,不知如何才好,陈长青反倒替他们打圆
场,又向我连连施眼色,示意我别再多说甚么。
老实说,若不是看得出,他们一直生活在极度的痛苦中,实在十分可怜,我真不会原谅
他们刚才对陈长青的这种态度。
当下,我略摆了摆手,表示算了,陈长青才又道:“我看,有可能,现在登广告的那少
女,就是当年曾神秘出现的那个小姑娘。”
我皱着眉:“要找这个登广告的少女,不是困难,这件事交给我好了。”
我想到的是小郭。小郭的私家侦探业务,越做越广,已是世界十大名探之一,那少女曾
出入那么多家报馆,要找出她来,自然不难。
我说着,就走到放电话的几旁,拿起电话,小郭变成名探,架子挺大,平时连电话都不
怎么听,不过我有他私人电话的号码,自然一拨就通。他听到了我的声音,高兴莫名,我把
情形对他说了一下,他一口答应,而且道:“有这样的线索,要是三天之内,不能把这个少
女找出来,那我也别混下去了。”
我哈哈大笑:“先别夸口,很多时候,事情的表面越是简单,内情就越复杂。”
小郭大声道:“包在我身上,一有结果,立刻就和你联络。”
我放下了电话:“只要一找到那个少女,一切都可以明白,何必瞎猜。”
陈长青有点不好意思,自己敲着自己的头:“真是,这是最简单的办法,怎么会一时想
不起来,我看,我们也该告辞了。”
敌文同夫妇又说了一些客气话,送我们出来,经过大厅,我在那座玉雕像面前,停了相
当久,欣赏着。整座玉雕像,当然不单是工艺精绝,而且实实在在是一件非凡的艺术品。从
雕像看来,敌家健生前,高大英俊,颧骨略高,鼻子十分英挺,粗手大脚。这样可爱的一个
青年人,二十岁出头就去世,难怪父母要伤心怀念一辈子。
我终于转过身来,我看到敌文同夫妇,都在偷偷垂泪。我也没有甚么话好说,只是长叹
一声,拍了拍敌文同的膀子,敌文同长叹了一声,老泪纵横,陈长青拉了我一下,和我一起
走出去,敌文同夫妇尽管伤心,但还是礼数周到,一直送到了大门口,真奇怪何以刚才,他
们会对陈长青的态度,如此恶劣。
我们上了车,陈长青立时道:“那个王玉芬,他们连提也不给提的女孩子,是家健的爱
人。”
我“哦”地一声:“老人家不赞成?”
太爱自己儿女的父母,往往对自己儿女的爱人,有一种莫名的妒嫉,却不知道,儿女长
大,一定会寻觅异性,绝不能只满足于父母之爱。
陈长青叹了一声道:“不,不过他们认为,家健是被王玉芬杀死的。”
这倒很出乎意料之外,我立时道:“怎么一回事?敌家健死于谋杀?”
陈长青一挥手:“当然不是。死于一次交通意外,说起来也真是命里注定,出事之前不
多久,敌家健二十一岁生日,敌文同买了一辆车子给儿子做生日礼物,家健有驾驶执照,而
王玉芬没有,那天,王玉芬来探家健,王玉芬比家健小一岁,年轻女孩,好动又活泼,吵着
要开车子。”
陈长青讲到这里,我已经可以知道以后发生甚么事了。
简单地来说:王玉芬吵着要开车子,她又没有驾驶执照,是不是曾学过开车,也成问
题。当时,敌文同夫妇反对,可是敌家健却禁不起女朋友的娇嗔,对他父母说,有他在身
边,不要紧的,而且乡间的大路宽阔,不会开车,也不要紧。
敌文同夫妇扭不过儿子,但还是对王玉芬极度不满。他们眼看着王玉芬开车,敌家健坐
在旁边,车子歪歪斜斜地驶向前去,驶出了他们的视线之外。
王玉芬和敌家健这一去,就没有再回来。车子驶出了不到一公里,就失去了控制,冲出
了公路,跌下了五十多公尺,王玉芬和敌家健,身受重伤,若是立刻得到抢救,两人可能还
不致丧生,但是路上来往的车辆不多,等到被发现,把人救出来,已经过去了二小时,伤
重,流血过多,两人奄奄一息,等到双方家长赶到,王玉芬先死了,敌家健只向他的父母,
看了一眼,也停止了呼吸。
这种惨剧,时有发生,局外人,看到报纸上有这样的新闻,至多长叹一声,说这是惨
剧,但是失去了亲人的,内心的惨痛,真是难以形容。
敌文同夫妇,于是一口咬定,自己的儿子被无知任性的王玉芬杀死,将王玉芬恨之切
骨。
我听到这里,不禁苦笑了一下:“王玉芬自己也死了啊,还恨甚么?”
陈长青摇头:“他们还是一样恨,而且连带也恨王玉芬的父母,听说,当时在医院的急
诊室外,敌文同就几乎没把玉芬的父亲掐死,骂他生出这种害人精的女儿,唉,也难怪他伤
心,而王家却怪他们不阻止,反怪家健害死了他们的女儿。”
我可以想像,两个丧失了儿女的家庭,如何互相埋怨对方的情形。有这样的一段往事
在,难怪敌文同夫妇刚才对陈长青的态度如此恶劣。
我想了一想:“你认为那个几年前曾出现过的小姑娘,和如今登广告的是同一个人?”
陈长青点头:“有可能。”
我又道:“她,你认为是王玉芬转世?”
陈长青深深地吸了一口气:“我向敌文同夫妇提出这一点,几乎没给他们用扫帚拍打出
来。敌文同还说,如果那女孩真是王玉芬转世。他拚了老命,也要把她掐死,替他儿子报
仇。”
敌文同的态度如何,倒可以不论,那登广告的少女,的确耐人寻味。她的行迳十分怪
异,有一点很难想得通:她为甚么要找敌家健?
就算她真是王玉芬转世,她明知敌家健死了,怎么还会去找他?
我一想到这里,陡然之间,豁然开朗,想到了整件事的关键,不由自主,“啊”地一
声,叫了起来。由于我平时不大惊小怪,是以这一叫,把驾车的陈长青吓了一大跳,他连忙
停住了车,向我望来。
我立时道:“我明白了,那少女的前生是王玉芬!”
陈长青忙道:“是因为那小姑娘,或者那少女的年龄,十分吻合?敌家健十周年忌辰,
那小姑娘看来十岁左右,如今十七年了,那登广告的少女,看来十七八岁,她一定立即转世
再生。”
我道:“这固然是因素之一,还有那广告上的用辞,看起来很普通,但是辞意十分有含
意,看起来,是一双男女,在若干年之前分手,但是又相约在日后再聚,而到时,却有一方
失了约。”
陈长青“啊”地一声:“你是说,当年王玉芬和敌家健,临死之前,相约来生相会?”
我点了点头:“如果承认如今这个少女的前生是王玉芬,那么,就一定是这样,他们的
车子失事,受了重伤,被困在车中,最后死亡的原因是失血过多,他们必然会有一段极其可
怕的经历:知道自己伤重要死,但是神智却还保持一定程度的清醒。来生预约,一定在这种
情形之下约定。”
陈长青听得神情十分激动:“相约来生,何等动人的爱情故事!玉芬已经有了来生,家
健是怎么一回事,为甚么还不出现?”
我道:“作一些假设看看。”
陈长青兴致勃勃:“好,第一个假设是,家健的来生,在一个相当远的地方,所以无法
取得联络。”
陈长青的话,令得我陡然想起一件事,不由自主,打了一个冷颤:“我听说过,有一个
印尼科学家,和他的好朋友,相约了他死之后,一定会有再生,结果,他降生在新畿内亚,
深山的穴居人部落之中。”
陈长青张大了口:“不会吧……不会这样悲惨吧。”
我吸了一口气:“另一种可能是,由于两生之间,通常来说,都会不记得前一生的事,
所以今生的家健,根本不记得有这样的一个约会了。”
陈长青道:“那何以今生的玉芬记得?”
我道:“这十分罕见。据我所知,即使今生的家健没有了前生的记忆,但是由于某些因
果,今生的家健,如果见到了今生的玉芬,一定会爱上她。”
陈长青松了一口气,他十分重感情,我提出了玉芬和家健在自知必然难逃一死,有着
“来生之约”,他一直希望这一双男女,在今生会再续前缘,有一个美满的结果。
他道:“那就简单了,只要我们可以找到今生的玉芬,问问她有没有热烈追求她的青
年,这个青年,就可能是今生的敌家健,有趣,有趣。”
我摇着头:“这只不过是我们的想像,而且,也不是那么有趣。”
陈长青“哼”地一声:“相爱的男女,能够缘订来生,而且,又有美满的结果,怎么不
有趣?”
我叹了一声:“你怎么知道必有美满的结果?”
陈长青固执起来,真是无理可喻,他用力一下拍在驾驶盘上,大声道:“一定有的。”
我要是再和他争论下去,那真是傻瓜了,我道:“快开车吧。”
陈长青还在嘀咕,我也不去理会他,他驶出了没有多久,又在路边停了下来,指着路旁
的悬崖:“就在这里,车子失事,翻了下去,详细的情形怎样,敌文同不很肯说。“
我笑道:“当年,这宗交通失事,一定轰动社会,到图书馆的资料室去查一查,比听敌
文同流泪叙述好得多。”
陈长青“哈”地一声:“真是,我又没有想到,这就去,这就去。”
本来,我对这件事,并不是十分热切,但是推测起来,事情可能和前生的约定有关,那
就变成了一件十分值得深究的事,所以,对陈长青的提议,我立时点头答应。
陈长青看来比我还性急,把车子开得飞快,到了图书馆,就直奔时事资料室。
陈长青是这家图书馆的熟客,职员都认识他,不一会,微型软片,一盒一盒找了出来,
我和他各自分据一架微型软片的显示仪,查看着当年这宗交通意外的资料。果然,当年的报
纸,对之记载得十分详细,非但有新闻报导,而且有特稿,有几份杂志,更是一连几期,都
详细地记载着。
不但有文字,还有敌家健和王玉芬的照片。
才一开始看资料,我和陈长青两人,已经呆住了说不出话来。令得我们惊愕的原因,自
然在后面会写出来,先说整件事的经过,比起陈长青复述,敌文同告诉他的,详尽了不知道
多少,而且还有极其感人的经过,是当年这件交通意外,引起公众广泛注意的原因。
原来,车子失事,冲出了路面,跌下悬崖,敌家健和王玉芬,两人都身受重伤,同时被
震出了车厢。当时并没有立即的目击者,而两个当事人又没有留下话就死了,所以真正的情
形如何,无由得知,但是按首先发现他们的一批郊游归来的青年学生描述:车子搁在悬崖的
大石上,被几株树阻着,毁烂不堪,两个伤者,敌家健和王玉芬,满身是血,处在一种十分
罕见的情形之下。
敌家健的左臂,紧紧勾住了一株打斜生出来的树杆,双脚抵在岩石上,支持着他的身
子,不致跌下几百公尺深的悬崖——在悬崖之下,是波涛拍岸的海。
敌家健的右手,紧握着王玉芬的右手,两人的十只手指,交叉着,紧握一起。王玉芬的
左手,还紧抓着敌家健的手腕。王玉芬如果不这样子,她的身子就会无所依靠,直向悬崖下
的大海中跌下去,她身子悬空,全靠敌家健抓住了她!
根据这样的情形推测,很容易得到结论:他们受了伤,被震出车厢,王玉芬本来曾向悬
崖下直摔下去,可是,同时被震出车厢的敌家健,却及时抓住了她的手,同时,又勾住了树
杆。
王玉芬单是一只手抓住敌家健不够,所以才又抓住了敌家健的手腕。
敌家健虽然抓住了王玉芬,使玉芬不至于跌下悬崖去,可是由于他自己受伤他很重,一
手拉住了王玉芬,一臂勾住了树枝,已经使他用尽了气力,再也没有力量把王玉芬拉上来,
他自己自然也不能攀上去求救。
于是,一切就在那一霎间停顿,他们两人,眼看着鲜血迅速地离开自己的身体,完全没
有别的行动,可以解除他们的厄运。
这情形,和敌文同告诉陈长青的经过,大不相同,敌文同并没有说出这种情形来。
敌文同不说出真实的情形,只说是救援者来得太迟,以致流血过多而死,原因也很容易
明白。死者的确因失血过多而死,但是却是在那样的情形之下失血过多而死!情形绝不普
通,而且十分感人。
我和陈长青一知道了当时的情形,互望了一眼,想起了一个相同的问题:如果敌家健松
手,放开王玉芬,他应该可以攀上悬崖去,他如果能攀回公路,自然有经过的车子会发现
他,他就有很大的机会获救。
自然,他如果放开了玉芬,玉芬万无生理——重伤之后,跌下悬崖,如何还有生望?
敌文同夫妇那样恨玉芬,理由也更明显,他们认定王玉芬害死敌家健,不单是由于王玉
芬坚持要驾车,也是由于出事之后的情形,出事之后,如果玉芬肯牺牲自己——敌文同夫妇
一定这样想:如果王玉芬肯自己松手,敌家健可以攀回路面。
这自然也就是敌文同不肯把真实的情形讲给陈长青听的原因。
动人的事还在后面,当两人终于被救起,救护人员,无论如何,也无法分开敌家健和王
玉芬紧握着的手。他们的手指和手指交叉紧握着,由于当时情形危急,救护人员只好由得他
们的手紧握着,进行急救。
到了医院,抢救人员仍然无法将他们的手分开,一直到他们死,他们的手始终互握着。
双方的家长赶到,看到了这样的情形,也有一些记者在场,当时在医院,有一场剧烈的
争吵。
王玉芬的父母,看到了这种情形,一面伤心欲绝,一面提议:“他们既然至死都不肯分
开,就让他们这样子合葬了吧!”
敌文同的哀痛,根本令他失了常态,他当场就破口大骂,一面发了疯也似,想把紧握着
的敌家健和王玉芬的手分开,拿起刀来,要把王玉芬的手腕切断,被在场的人拉住了,没能
成功。
虽然敌文同夫妇坚持要把两人分开,但是却一直没有法子做到,两人的手,像是生长在
一起了,到最后,实在没有办法,两人的尸体,一起送进焚化炉火葬。
这自然也是这宗交通失事能使报章杂志不断详细报导的原因。
还有许多报导,双方家长互相指责对方。而令得敌文同夫妇怒发如狂的是由于两人一起
火化,骨灰全然无法分得开,两家各分了一半,自然是两人共同的骨灰,这又加深了敌文同
夫妇的悲痛和恨意,难怪陈长青提及如今登广告的少女,可能是王玉芬转世,敌文同夫妇的
反应加斯强烈!
看完了所有资料,我和陈长青两人,呆了半晌,说不出话来。
过了好一会,陈长青才喃喃地道:“这……真是……他们……的来生之约,一定是在他
们自知不能活了,才订下的!”
我皱着眉:“真令人震栗,想想看,他们互望着,流着血,没有人发现他们,在这样的
情形之下,眼看生命离自己越来越远——“
陈长青不由自主发抖,我也停住了不再讲下去,因为这种情形,真是太悲惨了。
死亡,如果猝然发生,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完成,那并不如何可怕,可是,像敌家健王玉
芬这样的情形,那真叫人一想起就遍体生寒。
现在,该说说为甚么一开始看资料,我和陈长青就大吃一惊了。
应该说,首先吃惊的是我,看到了王玉芬父母的名字:王振强、赵自玲。这两个名字,
一点也没有甚么特别,我吃惊的原因是,各位还记得一开始时记述的那不断的来信,“不知
如何才好的父母”吗?在这个署名之后,有着签名,正是王振强和赵自玲。在他们附来的回
邮信封上,收信人是王振强、赵自玲!
我自然也立时想起,他们的信中,曾提及“我们已经失去过一个女儿”,当然就是王玉
芬!
陈长青因为不知道我收到过这样的来信,所以,这两个名字,对他来说,一点意义也没
有,不会引起任何反应。但是,我们看到了王玉芬的照片,都怔住了。
陈长青“啊”地一声:“这女孩子,我肯定见过。”
照片中的王玉芬,看起来瘦削而清秀,我立时道:“你当然见过,我也见过,就在我们
离开住所时,在对街留意我们的那个女孩。”
陈长青“啊”地一声,惊愕莫名:“对,至少,两个人极其相似,我不知道一个人的前
生和今生,连容貌也会相似。”
我道:“我也不知道会有这种情形,但是我相信,其间一定还有我们不明白的曲折在。
王玉芬的父母,最近一直在写信给我——“
我把王玉芬父母的来信,向陈长青提了一下,陈长青用力一拍桌子,令得资料室中的其
他人,向他怒目而视,他立时压低了声音:“那少女,是他们的另一个女儿:王玉芬的妹
妹,王玉芬的今世,就是她自己的妹妹,姊妹两人,自然相似。”
我也不禁“啊”地一声:“不必麻烦我们的郭大侦探了,我想,白素已不知和那少女谈
过多少话了,我们赶快回去吧。”
陈长青极其兴奋,草草把其他的资料看完,我则去打了一个电话给白素,白素一听得我
的声音,就道:“你快回来。”
我立时道:“留住王小姐,别让她走。”
白素的声音略现讶异:“你知道她在,那不足为奇,怎么知道她姓王?”
我道:“说来话长,我已经知道了很多,我和陈长青立刻就赶回来。”
白素道:“那最好,我虽然已请她进屋子,可是她坚持要见了你才说一切。”
我放下电话,就归还了资料,仍然由陈长青驾车,赶回家去。
进门,就看到白素和那少女对坐着,看来那少女仍然没有说过甚么。一看到了我和陈长
青,略带羞涩地站了起来,欲语又止,白素道:“这位,是王玉芳小姐。”
我和陈长青互望了一眼,姊姊叫王玉芬,妹妹叫王玉芳,再现成都没有。
王玉芳还是没有说甚么,白素道:“王小姐说她有非常为难的事情,说出来,绝不会有
人相信,所以,她不好道如何说才好。”
我望向王玉芳,沉着地道:“一个人,带着前生的记忆,再世为人,其实并不太奇特,
怎么会没有人相信?”
我这两句话一出口,王玉芳陡然震动了一下,一时之间,不知所措之极。任何人,心中
深藏着的秘密,以为绝没有人知道,突然之间,被人讲了出来,都会有同样的反应。白素听
了,倒并不怎么吃惊,因为她一定早已知道,王玉芳的父母,就是写信给我们的人,在信
中,曾提及他们的女儿,像是有着前生的记忆。
看到了王玉芳不知所措,白素过去,轻轻握住了她的手,和她一起,坐了下来。
王玉芳也握紧了白素的手,身子微微发着抖,我和陈长青都不出声,等她的精神回复正
常。
过了好一会,她才吁了一口气:“我其实早应该找你们,但是……我想,发生的事,这
样惊世骇俗,根本不会有人相信……唉,可是我实在太想念家健,又没有法子找到他,所
以……所以……”
陈长青立时道:“你放心,我们一定尽力,为你把家健从茫茫人海中找出来。”
王玉芳向陈长青投以感激的眼色。白素对于事情的前因后果,还一无所知,但是她就是
有这份耐性,一点也不急着发问。
我轻咳了一下:“那次意外的经过,当然极痛苦,不过是不是请王小姐可以忆述一
次?”
王玉芳低下了头,像是在回忆,又像是在深思,我趁她还没有开口,把她的情形,简略
地向白素讲述了一下。本来,王玉芳的前生是王玉芬,这还只不过是我和陈长青的假设,但
是在一见到玉芳之后,三言两语,这一点已成为肯定的事实了。
白素听我说着,王玉芳也抬眼向我望来,等我说完,王玉芳抢先道:“卫先生,你怎么
会想得到的?”
我作了一个手势:“推测得来的结论。”
王玉芳的神情有点激动,又过了好一会,她才开口,声音听来,却又十分平静。
她道:“出事的那天……我意思是指出事时,其实是家健在驾车。我开着车子离开,没
有多久,就发觉我不会驾驶,无法控制车子,家健帮我停了车,我们互相换了位置,就由家
健驾车。我们准备在附近兜一个圈子,就回家去。家健很喜欢开车,也喜欢开快车,敌家伯
伯绝对不许他开快车,他对我说了,可是一面说,一面却把车子越开越快。
“我和家健都年轻,其实我们都不觉得开快一点有甚么不好,我一面提醒他,车子越来
越快,一面还不断地笑着。
“而就在这时候,有一只口中衔着小猫的大猫,突然自山边窜出来,家健若不想避开他
们,也就没有事了,可是他却想避开,车子一扭,就失去了控制,冲出路面,冲向悬崖。
“一切,全在一刹那之间发生。我时时在想,那只根本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野猫,早半
秒钟窜出来,或是迟半秒钟窜出来,就甚么事也不会发生了。可是它偏偏在这个时候窜出
来,我和家健两个人,就因为这样偶然的一件事,而一切都改变了,这或者可以说是命运
吧,唉。”
王玉芳的声音很清脆动人,她缓缓地叙述着,神情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哀切。
这时。她在忆述着当日发生的事,当日事件的经过,根本没有别人知道,但王玉芳自然
知道的,因为她的前生是王玉芬,是当日在车子中的两个人之一!
------------------
第三部:死也不放开,生也不放开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王玉芳略停了停,舔了一下唇:“那一霎间的事,真是记不得了,我只记得一下剧烈的
震汤,一定有一个极短暂的时间,失去了知觉,然后,就是痛楚,四肢百骸,里里外外,没
有一处地方不痛,再然后,我就看清楚了自己的处境,我全身悬空,只有一只手被家健紧握
着,我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抬起另一只手来,抓住了家健的手腕。”
这些经过,我和陈长青都知道,但这时由“当事人”亲口说出来,听来还是极之惊心动
魄。
王玉芳的身子震动了一下:“那时,鲜血自我头上不知甚么地方流下来,稠腻腻的,令
得我视线模糊,但是我头脑都还十分清醒,我立即看清楚了家健的处境,家健的身上各处,
也在不断冒着血,样子可怕极了,他的一只手臂,紧紧勾在树枝上,他在上,我在下,自他
身上涌出来的血,一串一串,滴在我的身上,当时,我只看到他的口唇在动,完全听不到他
的声音,但忽然之间,我的听觉恢复了。
“我听得他用嘶哑的声音在叫:『玉芬,千万不要松手,支持下去,支持下去。』我喉
头一阵阵发甜,无法出声,只好点着头。
“这时候,甚么声音都听到,自他身上流下来的血,溅在我身上的拍拍声响,听起来真
是可怕。我也听到下面的海沟冲击,公路上有车子疾驶而过。我们开始叫唤,可是我们的声
音不大,在路面上经过的车子,又看不到我们,所以根本无法听到!
“我知道这样下去,绝不是办法,家健用尽了气力,想把我拉高一点,使我也可以抓住
树枝,可是他真是用尽气力了,一点也没能拉动我,我还是悬在空中,我忽然哭了起来,出
事之后,我直到这时才哭,泪水……和着血一起涌出来,我哭着:『家健,放开我,让我跌
下去,你可以自己攀上去求救。』我一面说,一面松开了抓住他手腕的手。
“可是,我们的另一只手,却手指交缠着,紧握在一起,他不放手,我无法松得开,而
他又是握得这样紧,这样紧……”
陈长青听到这里,长叹了一声:“握得真紧,没有力量可以使你们互握着的手分开
来。”
王玉芳震动了一下,低下头去,我们都没有催她。
过了好一会,她才又缓慢地开始:“奇怪的是,当时我们都知道,生命在渐渐远离,可
是我们的心境,却十分平静,连身上那么多处伤口,也不觉得十分疼痛。开始,我们都认为
是可以获救,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,血不断涌,我们都知道没有希望了。
“这一段过程,有好几次,耳际变得甚么声音也听不到,只听到血在流,我不断地在
讲:家健,放开我,你自己爬上去,放开我,你自己爬上去。可是我不能肯定我在实际上,
是不是有声音发出来,那情形,就像是一个十分真实的梦境。可是有几次,我用尽了气力在
叫,总是发出声的,因为我突然听得家健说:不放开,不放开,死也不放开,生也不放开。
“我一听得他这样说,想睁大眼,把他看得更清楚一点,可是不论我如何努力,看出
去,他总是模模糊糊,看不清楚,我们认识了一年多,虽然互相都知道深爱着对方,但是他
不是一个热情奔放的人,从来也没有那么强烈地向我表示爱意。
“当时,我只觉得心血沸腾,似乎又多了力量,我立时道:『好,家健,我们来生也要
在一起』。家健道:『你去投你的胎,我投我的,我们来生要在一起,一能行动,就要相
会。』
“我道:『是,不过……来生是甚么样的?』家健道:『我也不知道,但是总有来生
的,如果没有,那太悲哀了!』
“我知道他还说了一些甚么,但是听不清楚,生命已远离我,我知道自己快死了,死了
之后怎么样,完全不知道,心里十分恐慌,但是我却牢牢记得和家健的来生之约,我相信他
也一定记得。我最后听到有很多人在叫,大约是那群青年人发现我和家健时发出的呼叫
声。”
王玉芳讲到这里,又停了下来。
这时,我、白素和陈长青三人,都相当紧张。王玉芬死了,她转世,变成王玉芳,其间
的过程如何?如果王玉芳有全部记忆,那将是研究前生和今生、研究转世珍贵之极的资料。
王玉芳这时,清秀俏丽的脸上,现出十分迷惘的神情。
她向我们每人看了一眼,才道:“丧失了最后知觉之后,一直到又恢复了有知觉,这其
间,究竟发生了一些甚么事,我只是一片空白。”
我“啊”地一声,明显地表示了失望。
王玉芳摇着头:“我没有像一些书籍中所写的那样,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光环,听到了
音乐;也没有感到自己向上升去,看到了自己受伤的身体,甚么也没有。就像是倦极了,自
然而然入睡,等到一觉醒来,已经是另一个境界,甚至连梦境也没有。”
我叹了一声:“身体和灵魂之间的关系最难测。似乎每一个例子都是个别的,没有一定
的规律,每个例子,都有不同的遭遇。”
王玉芳没有表示甚么意见,白素道:“你父母说你不到一周岁,就会沉思,你感到自己
『一觉睡醒』,是甚么时候?”
王玉芳道:“小时候的事情,真是不记得了,只记得一直在想:有一件事很重要,一定
要记起它来,可是怎么也记不起,等到有一天,突然想起了我和家健的约会时,我已经十
岁,一想起了这件事,所有的往事,都在极短的时间之中,一起想了起来。
“我又害怕又兴奋,虽然亲如父母,我也半个字都不敢透露。我父母觉得我自出生以来
就有点怪,那可能只是我下意识的行动。
“回复了记亿之后,第一件事,就是到图书馆去找当年的资料,知道了我和家健死了之
后的一切经过。
“在我们十周年的忌辰,到了家健的家中,我不知道自己是何以会转世成为自己的妹
妹,或许,在我死的时候,我母亲正怀孕,而我的意识是要回家,所以,灵魂进入了当时的
胎儿中。”
王玉芳说到这里,用询问的目光望着我。
我摊了摊手:“或许,没有人知道在甚么样的情形下,灵魂和肉体相结合。”
王玉芳叹了一声:“我去的时候,我多么希望家健已经在了,变成了他自己的弟弟,或
是他的邻居,可是我失望了。由于我知道敌伯伯和敌伯母恨我切骨,我自然绝不敢讲自己是
甚么人,我只希望能见到一个和我应该差不多年纪的男孩子,而且我绝对肯定,只要我们一
见面,就可以互相知道对方是甚么人,不论他的样子怎么样,我们之间的爱情都会延续下
去。
“那次从敌伯伯家中回来,我知道家健没有『回家』,情形和我有所不同,那我就得费
功夫去找家健。可是一个十岁的小女孩,行动没有太多自由,我已经尽量有时间:我根本不
上学——这是父母认为我古怪之极的原因之一。
“我也不做其他小女孩做的事,因为在形体上,我虽然只有十岁,但实际上,我的智力
超越了年龄,我尽一切可能找家健,越是人多的地方,我越是去,我有信心,就算是几万人
的场合,只要他在,我一下子就可以认出他来。可是,一年又一年过去,我一直没有找到
他。”
王玉芳的神情,越来越是黯然,声音也越来越低沉。陈长青叹了一声:“王小姐,你应
该考虑到,再生的家健,可能在地球的任何角落,不一定就在本地。”
王玉芳道:“我自然想到过,可是……我有甚么能力……在全世界范围内找一个人?登
了那么久广告而没有回响,我已经知道他不在本地,所以,我才……才想到了卫先生……想
请他帮助,可是……实在不知道如何开口才好。”
我还没有回答,白素已经道:“你放心,我们一定尽一切力量帮助你。”
王玉芳神情感激,眼神之中,充满了期望。这种情景,本来十分感人,但是我由于想到
一个关键性的问题,对整件事,感到并不乐观,所以我只是保持着沉默。
陈长青十分起劲,就他所知,向王玉芳解释着前生和今生之间,可能出现的种种不可预
测的情形,但是他只讲了一半,就有点脸红耳赤地住了口,因为王玉芳虽然听得很用心,但
是在应答之间,很快就令陈长青明白,她在这方面的所知,多过他不知多少。
这很正常,因为王玉芳本身,有着前生的记忆,她自然一直在留意有关方面的书籍、报
导和资料,陈长青怎能及得上她这方面知识的丰富?
我想了好久,才道:“其实,你可以向你父母说明这一切,你父母一直在写信给我们求
助。”
王玉芳现出了迟疑的神色来,叹了一声:“我已经尽量使自己正常,可是看起来还是怪
得很。我不向他们说明自己的情形,一则,是由于事情本身,太惊世骇俗;二则,敌伯伯他
们恨我,我父母也恨透了家健,如果他们知道我在找寻家健,一定会反对和阻挠。”
我不禁有点骇然:“不会吧,他们知道你再生了,就不会恨家健了。”
王玉芳摇着头:“很难说,我再生了,他们自然喜欢,但是他们一定会想:原来应该有
两个女儿,现在只有一个,还是失去了一个女儿。”
王玉芳的这几句话,不是很容易理解,但却又是实在的情形。这情形多少有点特别,因
为王玉芬转世,恰好是降生在自己家里,那就会令她的父母觉得始终是少了一个女儿。
如果王玉芬转世,生在别人家里,长大了之后又回家,那么她的父母自然高兴不尽。
白素“嗯”地一声:“是的,普通人不容易接受你的经历,暂时不必说,等找到了家
健,再说……或者根本不说都可以。”
陈长青问:“王小姐,你说,就算是几万人的场合,只要他在,你就可以指出他来?”
王玉芳蹙着眉:“我只能说……我感到我可以做到这一点。”
陈长青吸了一口气:“你的感觉,无疑十分强烈,那么,你是不是感到他已转世?还是
他可能根本没有转世?”
这个问题十分重要,因为如果敌家健根本没有转世,王玉芳自然找不到甚么。
而灵魂不转世的例子极多,极有可能。
可是,对于这个严重的问题,王玉芳连想也不想,就道:“他一定已经转世,我的前生
记忆恢复,我就有强烈的感觉,感到他活着,在不知甚么地方,活着。”
王玉芳说得如此肯定,这令陈长青感到十分兴奋,他一直希望事情有一个美满的结局,
看来,他准备倾全力去帮助王玉芳,去寻找转世后的敌家健。
他滔滔不绝说了许多计画,包括在全世界各地报章上刊登广告,而且拍拍胸口,说这些
事,都可以交给他来办理。
王玉芳自然十分感激,我们又谈了一会。本来,我以为可以在王玉芳的经历之中,得知
一个人转世的详细经过情形。但是根据王玉芳的叙述,我自然失望。而且我相信王玉芳所说
的是实情,她没有理由对我们隐瞒甚么。
生命本身极其复杂,到现在为止,虽然各方面都在尽力研究,可是所得的真实资料极
微,尤其在有关前生、今世、转世这一方面。
两生之间,经过了甚么样的过程,如何从一生到另一生,这其间的详细情形如何,却没
有人可以讲得出来,就像王玉芳所说的那样:倦极而睡,等到一觉睡醒,已经是另外一个局
面了。
在“熟睡”中,当然一定曾有许多事情发生,但是连当事人都无法知道,旁人更是不得
而知了。
生命的奥秘,或许也在于此,若是一切过程尽皆了然,生命还有甚么秘密可言?
谈了一会,白素建议王玉芳和我们保持经常的联络,并且,不必对她父母提起曾和我们
见过面。王玉芳一一答应,白素送她到门口后回来:“事情真是奇妙之极。”
我道:“奇妙?但是我却认为不是很妙。”
陈长青立时一瞪眼:“为甚么?”
我早就想到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,所以立时道:“为甚么只是转了世的王玉芬在找寻敌
家健,转了世的敌家健,何以不寻找王玉芬?”
陈长青道:“你怎知道他不在找她?或许,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,有一个十七岁的青
年,正肝肠寸断,在寻找他前生的情人。”
我摇头:“你这样说法,极其不通,敌家健若是转世到了巴西,他何必寻找,迳自到这
里来就可以了。”
陈长青怔了一怔:“他又怎知王玉芬转世之后,还在她原来的家庭之中?”
我道:“关键就在这里,他不知道,但是他至少该回来看看,王家可有甚么巴西青年、
冈比亚青年、印度青年出现过?不论他现在变成甚么样子,王玉芳都可以一下子就认出他
来,他没有来过。”
陈长青虽然一心要美满的结果,但是这个关键性的问题,他未曾想到,而且,那无可反
驳。
白素迟疑了一下:“或许,转世的敌家健,由于不可知的原因,未曾恢复前生的记
忆?”我点头:“这是最乐观的推测。”
陈长青叫了起来:“卫斯理,你想推测甚么?”
我叹了一声:“我不知道,真的,无从推测起,有几百个可能。”
陈长青沉声道:“我们应该相信王玉芳的感觉,她说她感到敌家健已然转世,好好活
着,只是不知道在甚么地方。据我想,我们由近而远扩大开去,我要去见一见你那个大侦探
朋友,叫他不必去找那少女了,在敌文同住所附近,去找十七岁左右的男孩子。“
我笑:“怎知道一定是男孩子,女孩子不可以么?我不认为在转世的过程之中,灵魂有
自由选择身体的自由。”
陈长青道:“女孩子也不要紧,她们一样可以——“
他没有说下去,停了一停,又道:“我还要到生死注册处去查,查一切十七年前出世者
的纪录。”
我叹了一声:“看来非这样不可了。”
陈长青说做就做,我把他介绍给了小郭,小郭的侦探事务所,动员了三十名能干的职员
去查这件事,在敌文同那屋子附近,十六七岁的少年,都找了出来,陈长青还约了王玉芳,
一起去看访那些人。
可是一连十天,一点结果也没有。
十天之后的一个晚上,陈长青和王玉芳,一起来到我家里,王玉芳的神情,十分忧郁,
白素安慰她:“才找了十天八天,算得甚么,玉芳,你得准备十年,甚至更长的时间去找
他。”
王玉芳陡然间:“为甚么只是我找他,而他不来找我?”
她也觉察到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了。白素向我望了一眼:“可能他受到了环境的限制,不
能来找你,或者,他在我你,你不知道。”
王玉芳低叹一声:“家健要找我,其实很容易,他只要到我家来就可以……他一来,我
就可以知道他是谁,奇怪的是……是……”
她讲到这里,迟疑着没有说下去,我道:“你想到甚么,只管说,我们相信你的感觉极
其敏锐,尤其对家健,有超乎寻常的敏锐。”
王玉芳吸了一口气:“这十天,我一直在家健的家附近,我有强烈的感觉,他不会在别
处,就在那里,一定就在那里。”
我们都不出声,因为感觉再强烈,也只是她的感觉,别人无由深切体会这种感觉是甚么
样的。
王玉芳的神情有点焦急,她略为涨红了脸:“真的,这种感觉,在我十岁那年,到敌伯
伯家去的时候,我就有了,我甚至感到他……就在原来的家。”
我“啊”地一声:“会不会他一直未曾转世,还以灵魂的状态存在,那就容易使你有这
种感觉。”
王玉芳道:“不会,如果那样,就应该我在何处,就感到他在何处,为甚么我会感到他
就在原来住的地方呢?”
王玉芳说得如此肯定,十分诡异,我们互望着,虽然对于灵魂、生命,我们都有种种假
设,但其中真正情形如何,我们都不知道,所以也无从发表任何意见。
王玉芳向陈长青望了一眼:“像今天,我两次经过敌家花园的围墙,我就觉得家健就在
围墙内。可是陈先生却要我离去,他说我和玉芬长得很像,敌伯伯看到了我,会对我不
利。”
我道:“长青,这就是你不对了,玉芳始终要和他们见面的。”
陈长青叹了一声:“敌文同的情形,你见过,他若是知道玉芬已经转世,家健却还没有
着落,只怕他立即就会发疯。”
白素摇头:“这不是办法,玉芳如今有这样强烈的感觉,我看,明天我们索性带着玉
芳,一起去拜访敌文同。”
我立时表示赞同,陈长青望向王玉芳,王玉芳也点了点头,陈长青扭不过我们三个人,
就向王玉芳道:“好,明天早上,我来接你,准十点,我们在敌家的大门口见,一起进
去。”
决定了之后,陈长青送王玉芳离去,白素忽然道:“找不到转世的敌家健,陈长青和王
玉芳,其实倒是很好的一对。”
我脱口道:“甚么很好的一对,陈长青大她那么多。”
白素笑了起来:“大那么多?把王玉芬的一生算上,王玉芳比陈长青还大!”
由于王玉芳的情形是这么怪异,她和陈长青之间,究竟谁大谁小,也真难以计算。
我没有再说甚么,只是道:“希望她那种强烈的感觉,真的有效。”
白素沉思着,我们又讨论了一下转世的种种问题,就没有再谈论下去。
第二天早上,我和白素驾车向敌家去,到了敌家门口,看到陈长青和王玉芳已经到了,
车停在墙外,两人在车子里,见了我们,才一起出来。
王玉芳很有点怯意,陈长青在不住地给她壮胆,我们先约略商议了一下,推我去和敌文
同夫妇打交道。于是我们按门铃,敌文同走出来开门,铁门打开,我们一起走进去,敌文同
一看到了王玉芳,就陡地一呆,刹那之间,连面上的肌肉,都为之颤动,目光定在她的身
上,再也移不开。
王玉芳的神情也很奇特,本来,她大有怯意,可是进了花园,她整个人都像是变了,变
得四周围发生的事,看来与她完全无关,她全神贯注,缓缓地四面看着,口唇微颤,但是又
没有发出甚么声音。
敌文同终于忍不住,用冰冷的声音问:“她是谁?”
我笑着:“敌先生,先进去再说。”我一面说,一面示意王玉芳也进去。
可是王玉芳不知专注在甚么事上,她竟全然未觉,直到白素碰了她一下,她才道:
“我……想留在花园,让我留在花园里。”
她的神态,有一股莫名的怪异,我们互望了一眼,不便勉强她,就由得她留在花园中,
其余人一起走向屋子。敌文同的神态,始终极其疑惑。
一直到进了他的书房,敌太太也来了,敌太太先在屋子门口,向王玉芳望了几眼,她
道:“那个女孩子,就是那个……一定就是她。”
敌文同脸色铁青,盯着陈长青,我道:“谁也不准乱来,敌先生,发生在这女孩身上的
事,同样也可能发生在家健的身上。”
听到提及了家健,他们两人的神态,才比较正常。但还是充满了疑惑。于是,我就先从
汽车失事时,是由敌家健在驾车开始讲起,才讲了一半,他们两人就齐声问:“你怎么知
道?”
我就是等着他们这一问,我立时告诉他们,那是王玉芳说的,而王玉芳,就是王玉芬的
转世,他们以前曾见过的那个“奇怪的小姑娘”,和近月来刊登广告的少女,就是她。
敌氏夫妇的神情激动莫名,敌太太厉声道:“把她赶出去,赶出去。”
敌文同四面团团乱转着,一面叫道:“打死她,打死她。”看他的动作,像是在寻找甚
么工具,以便把王玉芳打死。
我由得他们去激动,自顾自说着:“本来,我们不想带她来的,但是,她有强烈的感
觉,感到家健也已经转世了。”
敌文同失声叫:“她是甚么东西,家健要是转世了,我们是他的父母,应该最先知
道。”
我冷冷地望着他们:“她是一个转世人,有着前生的记忆,或许这就是使她能感到家健
已经转世的原因。你们有前生的记忆吗?你们没有这种能力!”
两人给我说得哑口无言,但是愤怒之情,丝毫不减,直到我又说了一句话,他们两人才
陡然震动了一下,一时之间,现出了不知所措的神情。
我讲的那一句话是:“她不但感到家健已经转世,而且感到他就在这里附近。”
他们震呆了片刻,敌太太首先哭了起来:“家健早就转世了?在这里?他为甚么不来见
我们?为甚么?他难道不知道我们是多么怀念他?”
敌太太一面哭着,一面抽噎地说着话,敌文同也跟着眼红了起来。
他把手放在妻子的手上,语言哽咽:“别这样,我才不相信甚么前生来世的鬼话,家
健……不是一直在陪着我们吗?那玉像……和家健在生时,又有甚么不同?看起来,还不是
活生生的家健?”
这时,听得敌文同这样说,我也不禁怔了一怔,那座玉雕像,毫无疑问,充满了生气,
但是无论如何,那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
若是说,敌家健转世,他前生的生命,进入了那座玉像之中,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。
虽然在各种各样的传说之中,人的生命和美玉之间,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,但是,人的
生命进入了玉之中,这实在难以想像!
我无比疑惑,向白素望了一眼,白素和我在一起那么久,早已到了不必甚么言语,就知
道我在想些甚么的地步,她看到我向她望去,缓缓摇头,低声道:“灵魂……不见得会进入
玉像之中。”
陈长青也陡然震动了一下,刹那之间,他也想到我们在讨论的是甚么问题了,他立时
道:“很难说,曾有一个灵魂,在一块木炭之中!”
敌氏夫妇却全然不知我们在讨论甚么,仍是自顾自一面抽噎,一面不断说着怀念家健的
话。我向白素和陈长青两人,使了一个眼色。
因为,我们既然想到了有这个可能,总得尽力去求证。
如果敌家健的转世,使他成了一座玉雕像,那么,在有些地方,倒是可以讲得通的,例
如他为甚么一直没有主动去找转了世的玉芬,玉像毕竟不是活生生的人,玉像有口,可是张
不开来,玉像有脚,可是不能动。
自然,也有神话故事之中,玉像、铜像,甚至是木像会变成活的例子,但是实在很难想
像,一座玉像,如何真会活动。
我一面迅速地转着念,一面急步向外走去,才一到大厅,我就看到了王玉芳。王玉芳站
在敌家健的雕像之前,怔怔地望着那雕像,纹丝不动。看起来,她这样站着,已经很久了。
她是那么专注地望着那座玉像,整个人都静止,极度静止,甚至使人感到她非但没有呼
吸,而且连体内的血液也凝结!
她的那种静态,给人的印象是,站在那里的王玉芳,根本也是一座雕像,而且,有生气
的程度,反倒不如敌家健的玉像。
我一看到了这种情形,立时止步,紧跟着我出来的是白素、陈长青,然后,才是敌氏夫
妇。他们两人一看到王玉芳在玉像面前,张口就要呼喝。
他们一张口,我和白素一起出手,一边一个,按住了他们的口,不让他们出声,同时,
陈长青也以极严厉的眼光,盯住了他们,我唯恐他们还要蛮来,用极低,但是极严厉的声音
道:“别出声。出一下声,我就绝不客气。”
或许是由于我的语气实在严厉,或许是由于眼前的情景,令得他们也感到不出声为上,
所以,他们一起点了点头。
我和白素松了一口气,放开了手,他们果然没有出声,只是喘着气。我再向王玉芳望
去,王玉芳仍然一动都不动地站在玉像面前。我们都跟着一动不动,注视着事态的发展。过
了好久,我双脚都因为久立,而略感麻木,才看到王玉芳的脸上肌肉,颤动了几下,接着,
她口唇也颤动了起来,然后,自她的口中,轻轻吐出了两个字来:“家健。“
这一下呼唤,声音极低,可是在一下低唤之后,她陡然尖叫了起来:“家健!”
她的尖叫声徒然划破了静寂,令得我们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。
她在一叫之后,就扑向前去,紧紧地拥住了那雕像,拥得极紧。在那一霎间,由于玉像
如此生动,我似乎在恍惚之间,感到玉像也在回拥着王玉芳,我连忙定了定神,自然,玉像
还是玉像,一切也没有动过。
王玉芳抱住了玉像,不住在说着话,声音急促,但是听得出来,充满了喜悦。
她在道:“家健,原来你一直在这里,我找得你好苦,我知道你一直在,一直在,没有
关系的,我早就说过,不论你变成甚么样子,我一下子就可以在几万人之中,把你认出来,
我们终于又在一起了、终于又在一起了。家健,我想你,我要告诉你,这些年来,我是多么
想念你,我……”她紧拥着玉像,我们不约而同,来到可以面对她的位置,只见她泪如泉
涌。
但是不论是神情还是语调,却又实实在在,满是喜悦和兴奋。
她不断地在说着,到后来,已听不清楚她在说些甚么,这种情形,若是两个人相拥着,
自然感人之极,可是此际,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,和一座玉像,这就令人有说不出来的诧
异。
敌文同夫妇骇然互望,陈长青一连叫了好几声,玉芳才不再对玉像说话,抹着眼泪:
“谢谢你们,我终于找到家健了,上次我来的时候,竟没有看到,不然,也不必又等了那么
多年!”
敌文同缓缓向前走去,未到玉像之前,忽然发出了一下低呼声,神情讶异莫名,急速喘
着气,叫:“快来看,这好像……有点不同了!”
敌太太连忙奔过去,看着玉像,也现出疑讶的神情来。这时,我也注意到了,玉像的脸
部,似乎更流动,更有生气,那种美玉的光辉,在隐隐流转,以致玉像看来,更像是活的!
前一次,我曾仔细的留意过这玉像,可以明显地感到不同!陈长青也有点怔呆,只有白素,
因为以前未曾对玉像注意过,所以没有比较,但这时,她也为那玉像的生动而感到惊讶。
敌文同的身子簌簌地发着抖,用发抖的手,去抚玉像的脸颊,颤声道:“孩子,真是
你?孩子——“
他已无法再说得下去,和敌太太两人,一起去拥抱玉像,连王玉芳也抱在一起,敌文同
夫妇互望了一眼,显然,他们对王玉芳的恨意,就在那一霎间消除了。
转世了的王玉芬,终于找到了转世了的敌家健。可是敌家健却成了一座玉像。
不过王玉芳一点也不在乎,她当天就没有离开敌家,敌文同夫妇给她整理了一间房间给
她住,并且,三个人合力,把那座玉像,移到了她的房间中,王玉芳宣布,那就是她的丈
夫,敌家健。敌文同夫妇自然也很高兴。可是,另外却有人极不高兴。
首先不高兴的是王玉芳的父母,到敌家去大吵大闹了很多次,可是王玉芳一再表示一切
全是她自愿,还把她转世的事说了出来,说这一切,全是命运的安排。
但是她父母仍然不相信,直到王玉方说,要是不让她这样,她就自杀,她父母总算没有
再逼她回家,只是派了好几个精神病专科医生,去替她作检查,而检查也没有结果,因为王
玉芳除了坚决把一座玉像当作她的丈夫,异于寻常之外,其余一切,都正常无比。
两个专家事后找到了我和白素,我问他们检查的结果如何,以下是两个专家和我们之间
的对话。
专家之一说:“这是一宗罕见的精神分裂症病例,患者完全投入了她自己的幻想之中,
而迷失了原来的自己。”
我皱看眉:“你们否定转世再生。”
专家之二喟叹:“卫先生,转世、再生,全是她自己讲出来的,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
明。”
我反驳:“可是她知道汽车失事时的一切详细经过。”
专家之一苦笑:“她自小到大,一定不断地听她父母讲述过关于她姊姊如何意外死亡的
事,这件事,对她来说,印象深刻无比,渐渐地,她就把自己当作了是她的姊姊,精神分
裂,于此开始。至于失事的经过,既然无从求证,不论她如何幻想都可以。”
白素不以为然:“她何以见了玉像,就肯定那是敌家健?”
专家之二道:“她进入了极度的幻想,自然看熟了敌家健的相片,那玉像,的确十分生
动逼真,她既然无法找到家健,心理上再也无法负担失望的痛苦,就把玉像当作了真人。”
我叹了一声:“当时你们不在场,玉像在见到了玉芳之后,神情完全变了。”
两个专家互望了一眼,过了片刻,专家之一才道:“如果你精神状态正常的话,那么只
能说当时的气氛相当动人,所以令你们起了心理上的幻觉。”
我和白素都没有再说甚么,只怕再说下去,两位专家要怀疑我们都有神经病了。
送走了两位专家,我对白素道:“任何事,一经所谓科学分析,就无趣之极,这件事本
身,结局虽然这样怪异,甚至可以说是十分悲惨,但十分浪漫动人。给他们一分析,甚么都
完了。”
白素苦笑一下:“或许,他们的判断是对的?”
我摇了摇头:“或许,谁知道!”
除了王玉芳的父母之外,另一个极其不满意的人,是陈长青。
当玉芳伴着玉像,再也不肯见他,他在我家里,一连醉了半个月,失魂落魄,可是却又
矢口不肯承认他失恋,他大声叫:“失恋?笑话,要是我争不过一座雕像,那我算是甚
么?”
我和白素都不敢搭腔,都只好希望,随着时间的过去,会治愈他心中的创伤。
整个故事,大家不妨细细想想,几乎没有一处,不是和命运的安排有关!
所以,把这个简单的故事,拿来作《命运》的附篇。
------------------
-
2022-05-01
-
2022-05-01
-
2022-05-01
-
2022-05-01
-
2022-05-01

股票分成,股票代操盘,炒股合作 炒股合作
吴老师QQ:2080053532
QQ:2654704327 QQ:2080053532
QQ:3532015225
推荐股票合作投资股票合作专业炒股黑马牛股长期合作
吴老师QQ:2080053532
QQ:2654704327 QQ:2080053532
QQ:3532015225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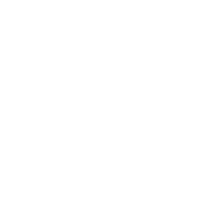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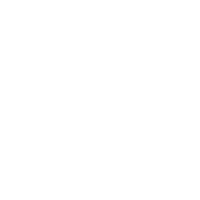
股票合作,炒股合作,股票合作分成,股市预测及股票推荐
吴老师QQ:2080053532
QQ:2654704327 QQ:2080053532
QQ:3532015225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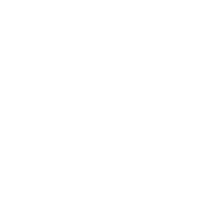
股票合作,推荐股票合作分成,证券投资,证券投资咨询
吴老师QQ:2080053532
QQ:2654704327 QQ:2080053532
QQ:3532015225

